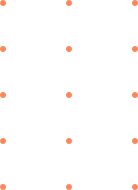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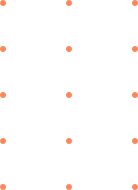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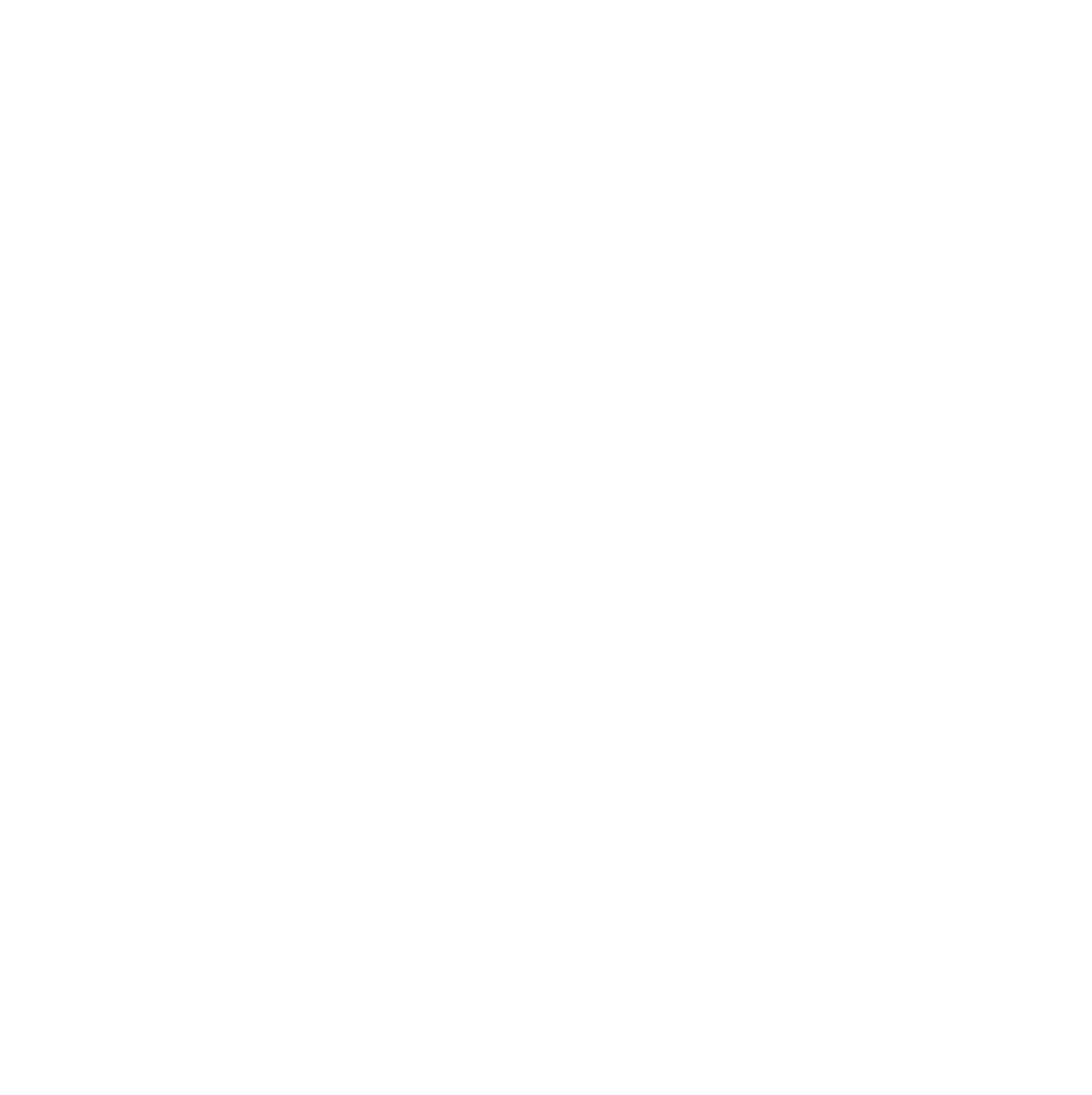
逢甲共善樓與淨零時代的新包浩斯運動一個時代精神詮釋的考察
文/曾梓峰
逢甲大學特聘客座教授
逢甲共善樓的誕生與爭議 一個時代事件的序曲
臺中的午後,陽光從水湳中央公園斜灑進逢甲大學新東校門,一棟壓低體量、細節繁複的建築映入眼簾。草坡延伸至屋頂,木格柵如呼吸般篩散光影,大片玻璃模糊了內外的界線。這就是近期在臺灣建築界引發最多議論的「共善樓」。
第一眼的感受,既顛覆又吸睛。它完全不同於傳統大學建築的嚴謹方格,反而像是一塊由風、流動的人群與自然共同雕刻的地形。兩層低矮的量體,配合N型軸線,串連層層外廊與穿透庭院。斜坡、穿堂、中庭、綠意庭園交織出一種導引移動的節奏。室內透過玻璃帷幕一覽無遺,大講堂、演藝廳、多媒體教室與跨域交流空間,都像被納入一張可自由穿透的網絡。這不是封閉的盒子,而是一個由格柵、坡道與光影織構的開放場域。
在校方的文本裡,共善樓被賦予「沉浸式學習、公共文化與開放校園」的承諾,以「共善大好、春風化雨」的價值敘事回應社會期待。這樣的語言很容易讓人信服,也讓人看見逢甲大學試圖以建築來體現治理願景與理想。
另一個鮮明印象,來自新校地「公園般」的氛圍。低矮量體與覆滿草皮的屋頂,與周邊庭院連成一片,宛如校園退隱於自然的生態島。這讓人自然聯想到當代城市最受關注的課題-Urban with Nature。這裡不僅傳達淨零、韌性與氣候中和的理想,更改寫了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日常關係。隈研吾將其命名為臺灣首座「地景建築」,呼應他一貫的「負建築」哲學:讓建築退隱、消失,追求共生。
第三個印象則來自它令人驚訝的工藝複雜度。191支鋼樑無一相同,1,750片玻璃各具尺寸,4,900片木格柵以千種比例拼合,甚至倒吊板的組裝也近乎無窮變化。對於習慣標準化生產的營造業,這是前所未有的挑戰。有人讚譽它為BIM與數位建模結合在地工藝的高峰,也有人質疑這是資源 浪費、誤差風險與維護困難的代名詞。
正因如此,社會對它的反應呈現兩極。支持 者稱它是「亞洲版新包浩斯」的雛形,認為它回應數位轉型與永續潮流;批評者則指出巨額投資對私校財務的風險、非標準化背離循環經濟、共享願景未必落實。甚至在設計界,亦有質疑它是否陷入大師自我複製的形式困境。
然而,這些爭議正揭示它的時代性。共善樓的評價從來不只是建築問題,而是一個社會問題。它把臺灣當前教育轉型、產業調整與社會共享的張力,集中展現在一棟建築裡。評論者必須承認,它或許不完美,但正因為它讓矛盾赤裸呈現,才值得被看作是典範轉型的鏡子。

共善樓作為時代精神詮釋的鏡子
「時代精神」(Zeitgeist)在建築史中總帶著厚重的分量。它不是抽象的哲學詞彙,而是時代如何理解自身、如何想像未來的形式化表達。黑格爾說它是「每個時代的理性展現」,一旦落入建築與藝術的領域,便化為牆壁、窗戶、街 道、城市肌理中的烙印。
然而,對時代精神的詮釋從來都不是平順的結果。它往往伴隨激烈的衝突,是在辯證與爭議中被淬鍊出來的。
歷史回顧:前衛與衝突
一百年前,現代建築的前衛大師們,在社會巨大變遷斷裂的前緣,與典範的轉型的衝突展開了戰鬥,透過對於「時代精神」積極的詮釋,提出了各種各樣大膽、前瞻而且統合的解決方案。
歐洲戰後廢墟中誕生了包浩斯。Gropius召集藝術家與工匠,提出「藝術與工藝統合」的口號,意圖以新的語言回應工業時代。短短十九年的歷史,包浩斯因其激進與衝突,被迫多次搬遷,甚至在歐洲被制度性的消滅,最後移植至美國。柯比意則以「住宅是居住的機器」提出現代建築理性與標準化的新秩序。當時他們被批評為「冰冷」、「不人性」。然而。歷史證明,他們真實回應以及引導了時代的需求表現,被證成他們揭露了現代性的起點。
21世紀的新挑戰
今天,我們同樣站在斷裂邊緣。這一次的危機不再是工業化的誕生,而是環境的反撲。氣候變遷與能源危機,使氣候中和成為不可迴避的課題;同時,AI、BIM、大數據等數位技術滲入生活每個角落,帶來效率,也加劇焦慮與不平等。更深層的,是階層、世代、文化的裂縫,使社會迫切需要一種新的「共感語言」。舊典範已然崩解,新典範仍在混沌中摸索。
在這樣的背景下,共善樓顯得格外具有「時代精神」的意義。它不僅是一棟建築,而是希望與矛盾同時凝結的隱喻。


共善樓作為「回應21世紀挑戰」的鏡子
我們可以把共善樓看作是一面鏡子。當我們凝視它時,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建築師的巧思,而是整個社會當前的矛盾,以及對於未來的欲望或渴望。渴望的是:
- 它的透明與穿透,象徵著對開放與交流的渴望;
- 它的客製化工藝,象徵著對卓越與獨特的追求;
- 它的綠坡與自然通風,象徵著對永續的期盼。
但同時,鏡中也浮現矛盾:透明是否真能帶來共享?卓越工藝是否意味資源浪費?永續設計能否在制度與維運中落實?這些問題不是缺陷,而是時代的真實。這些矛盾,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精神的縮影。它們不是建築的缺陷,而是歷史的真實。
與現代主義大師相比,隈研吾的「負建築」不再歌頌工業與標準化,而是回應環境與人本的需求。共善樓正位於這條弧線的另一端:既承襲數位技術的邏輯,又延續自然語言的語法。它是兩種典範之間的「混血」,亦是當代精神的縮影-在矛盾與混沌之中,孕育新的希望。
新歐洲包浩斯的浮現
「新歐洲包浩斯」(New European Bauhaus, NEB)是2020年歐盟在推動Green Deal時揭櫫的一項文化性計畫。它不僅是環境政策的延伸,更是一次歷史性再詮釋:在全球邁向循環經濟與氣候中和的壓力下,歐洲再度召喚「包浩斯」這個象徵,為二十一世紀尋找新的時代語言。
100年前的包浩斯的現身,回應的是工業文明的誕生,透過標準化、模組化,為大規模生產提供形式。今日的NEB,則是回應工業文明帶來的環境危機。它要求社會從線性的工業產品開發模式,轉向循環經濟與永續文化。這種轉折,不只是技術革新,而是文明典範的變化。
典範斷裂到重構:從線性的「工業文明」到閉環的「循環文明」
NEB運動的召喚,背後是歐盟委員會大規模新循環經濟方案「歐洲綠色政綱」(European Green Deal)。認為2050年實 現「氣候中和」,不只是減少碳排,而是一場邁向循環經濟徹底的社會系統轉型。經濟上從傳統「生產-消費-丟棄」的線性工業生產邏輯,轉向「修復-再生-循環」的閉環循環產業邏輯。重點是經濟從來不是可以單一切開的行動,政治與社會制度脈絡,以至於生活的展現,都必須是全面性的文明重構。能源、產業、建築、教育、日常生活,都必須重新設計。換言之,人類的生活方式必須被重寫。政策的語言往往是冷冰冰的。碳排放的數據、再生能源的比率,對多數人來說抽象而遙遠。要讓整個社會真正動員起來,必須有一種能夠觸動人心的文化語言。於是,「新歐洲包浩斯」(New European Bauhaus, NEB)被召喚出來。
新包浩斯運動的三重基調:永續、美學、包容
NEB提出了三個核心價值作為人類展現其社會發展行動,打造工業產品與邏輯的依歸:
- 永續(Sustainable):所有設計與建造都必須符合氣候中和、減碳與循環的邏輯;
- 美學(Beautiful):必須讓永續成為美好的體驗,而不是冷冰冰的技術;
- 包容(Together):優先關注社會脆弱群體,確保轉型過程中的公平與共享。
這三重基調,與其說是設計原則,不如說是文明宣言。它要把「必要的」轉換為「嚮往的」,把「政策的」轉換為「日常的」。
這三重基調被進一步展開為四個主題軸:「重新連結自然」、「重建歸屬感」、「優先關注脆弱群體」、「強調生命週期思維」。它們不僅是建築的指標,也成為城市治理與 生活方式的原則。NEB之所以獨特,不在於建立新風格,而 是透過「跨學科合作」、「群體參與」、「多層級治理」,把永續內化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。
在此脈絡下,NEB不僅是一個歐洲政策,而是一種方法論:它提供了如何閱讀與實驗當代建築的座標。當評論者回望共善樓時,它的透明性、自然化、非標準化工藝與社會共享願景,都能透過NEB的基調得到重新檢視。
NEB作為逢甲共善樓評析的互文框架
這種論述的策略,讓逢甲共善樓這棟校園建築,不再只是臺灣的孤立事件,而是被放置於全球文明轉型的語境中加以觀察的標的。如果說NEB是歐洲對氣候中和的文化翻譯,那麼共善樓則是臺灣在面對全球轉型時的一次在地實驗。
共善樓的評析
- 空間形式:從「樓」到「場」
逢甲校園從1990年代"Campus as Garden"到今日的共善樓,清楚展現典範的轉向。共善樓打破「樓層-走廊-教室」的分割模式,以斜坡、穿堂、開放中庭作為核心母題。學習不再侷限於課表與課室,而能在走動、停留、偶遇中展開:學生在樓梯間討論,教師在走廊與訪客交流,市民假日走進中庭喝咖啡。
這種模糊性,成為新的教育語言,也呼應NEB的語彙: 既是「重尋歸屬」,也是「回歸自然」。光與綠不僅是背景,更是教育的一部分;漫遊本身即是學習;校園邊界朝城市日常敞開。當然,這也引發疑問:當空間全然開放時,專注力是否受影響?傳統教學的安靜能否保存?這些張力正是新典範的必然考驗。
- 新建築形式與結構工藝:產業標準轉型的解構
若空間形式挑戰了使用邏輯,共善樓的結構工藝則挑戰了營造邏輯。191支鋼樑、1,750片玻璃、4,900片木格柵,每一件幾乎都是客製。這種「非標準化」明顯反叛了二十世紀現代主義的模組化。支持者稱之為「卓越工藝」與BIM技術的勝利;批評者則擔憂浪費資源與背離循環經濟。但從建築史的角度,這種嘗試具有深層意義:它迫使工匠重新學習,讓工藝在效率主義中重獲存在感,也將「全生命週期」納入考量。這正是NEB所強調的「重新連結自然」與「跨學科合作」-建築 不是冷酷組裝,而是一場文化再協商。
- 淨零與氣候中和:隱藏的能量
若僅以碳盤查檢驗,共善樓仍非零碳建築:複雜工藝增加能耗,維護依賴傳統能源。但它在設計中潛藏減碳潛力:透明立面引入自然光,減少日間照明;中庭與通風廊道降低冷氣需求;綠坡屋頂既隔熱,又能回收雨水並提供生態棲地。
這些元素若與能源治理結合,完全可能成為「碳中和治理」的試驗場。它的意義不在當下數據,而在於為未來制度接軌提供場域。這正呼應NEB的「生命週期思維」: 建築不是完工即止,而是長期治理的一部分。
- 使用與經營:新社會協議的醞釀
共善樓最大的挑戰,不在設計與工藝,而在使用與經營。它被設定為「跨界共創」的平台,但社會慣習的轉變需要時間。教師能否放下傳統課室?學生是否習慣開放學習?產業是否願意共享?市民能否自在使用私校空間?
答案並不立即可得。共善樓的未來取決於能否編織新的社會網絡。這正觸及NEB三重基調中最難的一環-「包容」。因為包容不是設計圖能解決的,而是一種社會協議的長期建立。
- 評論的凝視
作為一篇嘗試從回歸建築史角度的評論,很顯然共善樓不能僅以「功能成敗」來評價。對所有共同關切臺灣建築發展的朋友,它最大的價值,在於它真實地揭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困境。
它既追求卓越,也暴露矛盾;既提出希望,也帶來疑問。它的每一個木格柵、每一片玻璃、每一段斜坡,都是一種語言:它們在說,這個時代已經不再滿足於標準化的答案,但新的答案仍未清晰。
正因如此,它是一個「問題提出者」。而歷史往往記住的,不是那些「完美解答者」,而是那些勇於提出問題的人。
結語:從共善樓到臺灣的新包浩斯運動
- 矛盾的辯證
在建築史中,被記住的往往不是「完美」的建築,而是那些真實映照時代矛盾的作品。包浩斯校舍如此,它是現代性的序曲;龐畢度中心亦然,它把70年代對公共性的渴望具象化。這些建築之所以重要,不在於解決所有問題,而是把問題推到眾人眼前。
共善樓也是如此。草坡屋頂下,不僅是一棟教學樓,更是一種隱喻:臺灣高教處在裂縫中,營造產業在傳統與數位間掙扎,社會渴望共享卻受制於慣習。它把這些矛盾集中呈現,迫使我們直面。
- 一條百年弧線的連結
若把時間軸拉長,共善樓是百年弧線上的節點。
1920年代的包浩斯,語言是「工業化」:建築成為機器的朋友,以標準化回應大規模生產。
1970年代的龐畢度中心,語言是「透明化」:在冷戰與學運的氛圍下,建築翻轉內外,成為公共性的象徵。
2020年代的歐盟NEB,語言是「循環化」:建築被視為生命週期的一部分,是社會協議的載體。
2025年臺灣的共善樓,或許沒有帶來完整風格,也未引起國際轟動,但它清楚映照我們的矛盾:一方面渴望融入全球循環轉型,一方面受制於在地制度與產業。它是混血的產物,也是混沌的象徵,而這正是我們與世界接軌的契機。
- 矛盾的價值
有人或許認為這些矛盾意味失敗,但在評論的視角中,這正是它的價值。前衛建築不必完美,但必須真實。
共善樓揭示了數位建模與傳統施工的斷裂、永續口號與資源浪費的張力、校方願景與使用者習慣的落差。這些不是缺陷, 而是時代精神的具體化。正如Villa Savoye當年被批評「冰冷不實用」,卻最終成為現代建築的象徵,共善樓的成就或許也在於 「提出問題」。
- 新文明的前奏曲
放在全球語境下,意義更清晰:
包浩斯是工業文明的序曲;
NEB是循環文明的號角;
共善樓則是這場轉型在臺灣的回聲。
它未必成為經典,卻會被記住,因為它具象化了臺灣的矛盾與希望,成為「亞洲循環文明前奏的一個片段」。
- 評論者的最後凝視
若你作為一個觀眾走出共善樓,回望那片木格柵濾下的光影,會意識到:建築不是提供答案的器物,而是把人們帶到問題核心的媒介。
共善樓正是如此。它提醒我們,未來不是由既定答案構築, 而是由持續的實驗與提問推動。在這個意義上,它已超越一棟大學建築的範疇,而成為我們時代的隱喻。
分享: